在线配资开户网站 低成本生活与意义焦虑:逃走是解脱吗?
发布日期:2025-02-17 00:12 点击次数: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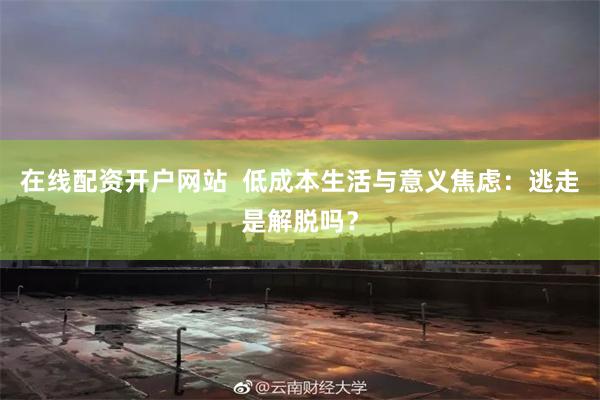
 在线配资开户网站
在线配资开户网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 Youthology,作者:小纠在线配资开户网站,编辑:阳少,题图来自:《凪的新生活 》
2024 年 8 月,非虚构写作者李颖迪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逃走的人》。她聚焦那些离开都市,来到鹤岗、鹤壁等资源枯竭型城市买房生活的年轻人。从旁观到亲身参与,李颖迪好奇这些年轻人为何做出"逃走"的决定,也想追问"出走后,ta 们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期许中的自由"。
去年末,在北京中信书店的一场对谈中,李颖迪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读书博主李乌鸦,探讨了在经济下行与数字化程度加深的社会里,鹤岗、鹤壁等城市如何成为一些年轻人的避风港?它们既有成为互联网时代"高地"的潜能,也更剧烈地映射了人际困境与意义焦虑。
"高地"原指地理上的偏远之地,在詹姆斯 · 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它象征着远离国家统治、避开主流控制的空间。而在刘海龙看来,数字时代的高地演变为一种因网络便利和低生活成本而形成的避世之所,让受困于日常工作与人际关系的人来到这里生活。
至于逃离,是为了追寻理想中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失去盼头后的微小抵抗?今天,或许每个人都在悄悄地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地"。
"逃离"往往并不理性,但总带着变好的期待
李乌鸦:《逃走的人》这本书是李颖迪走访了很多在鹤岗、鹤壁等地隐居的人,他们不喜欢在大城市里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就逃离大城市,去到所谓资源枯竭的小地方,寻找一种低欲望、低成本的生活。
我想先和颖迪聊聊,北京是一个你生活了很多年、大概也一度想"逃离"的城市,你当时去鹤岗生活了一段时间,有多少是来自于你不想在这儿待了,有多少是来自于你要为创作去取材。
李颖迪: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其实很长,从 2021 年关注到隐居吧(贴吧)时,我还是比较偏向记者打量别人生活的视角。但书的主体部分聚焦于 2022 年冬天我在鹤岗的亲身经历。老实说,那时我在北京确实待不下去了,自己的状态也很糟糕。大家应该记得那年的冬天——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我的状态很混乱,工作上也出现了问题。我曾开玩笑说,要用塔罗牌算算未来的出路,结果抽出的两张牌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恰好那个时候,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位在鹤岗的女生分享她改装房子的经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但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群体里有女性,和我的视角也很贴近,就想去看看。
李乌鸦:那刘老师呢,您也有过逃离的冲动吗?您怎么理解这些年轻人的选择?
刘海龙:好像没有特别想逃离的时候,另外也觉得没什么地方可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有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我觉得真正的隐居,不一定是地理空间上的,而是你个人的状态。包括书里写到的很多人,我能感觉他们还是很纠结,虽然身体上逃离了那个环境和空间,但如果心理上没有真正想明白,最后还是过不去那个坎。包括中国的老庄、道家,某种意义上也是让你去逃离或隐居。比如你可以完成最低的工作量,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在身体上决绝地斩断和此前的一切联系。
但我可以理解这些年轻人。大家还是受困于自己的发展,比如有人在一个工厂里工作,看不到未来,或觉得自己怎么做都做不好,面对这种困境,大家其实想做出改变。可能 99% 的人都会选择忍耐一下就过去了,或像我这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做出改变的人,其实是很有勇气的。
李颖迪:我觉得刘老师还是个偏乐观的人,可能也和您的年纪有关。我前阵子见到《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的作者周慧,她今年五十岁,生活在深圳边缘一个叫洞背村的地方。我和她聊的时候,她会说书里很多人因为确实很年轻,处于一个还想不清楚、很纠结、经常反复的阶段,包括我也是这样的,有时想明天就辞职离开北京,有时又觉得好像再工作一段时间也行。
很多人都是出于本能和直觉去做事。我和他们聊到为什么决定甩掉原来的环境,去鹤岗、鹤壁,导火索往往非常微小。过去长期的工作、生活、关系带来的痛苦是混合的,但已经在他们的身体上有了反应,于是他们本能地想要离开。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到鹤岗的第一天,也没看几套房子,就很冲动地买下。住进去后可能发现这房子也没那么好,后面可能还要换,要倒腾,要卖。很多时候,逃走的决定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在做出决定时,大家都带着一种会变好的期待,期待新的可能性。
从鹤岗到鹤壁,互联网时代的新"高地"?
李乌鸦:《逃走的人》写到的主要是在鹤岗、鹤壁生活的人,但颖迪辞职的第一站是去了海南万宁。像大理、万宁、清迈这些地方生活着很多数字游民,和去鹤岗的人相比,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李颖迪:我一开始也会觉得有阶层方面的差别,比如像那些数字游民,可能是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然后能做一些类似于 Web3 的东西,程序员还可以接外包的活,就能在清迈那些地方待着。但我对那些选择更多的人,会没那么感兴趣。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隐居的人,处在一个没那么多可选择的情况下,怎样去追求自由?
我认识的朋友也有去大理的,他说大理常有那种流动的聚会,有点像是嬉皮的感觉。但当我去鹤岗时,会发现大家其实彼此之间都很不了解,就像"饭搭子"似的,好像人对人展露出的好奇是非常微弱的,大家会有一些默认不要去碰的话题。当我去听他们讲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时,会发现他们还是被关系伤害过,比如说家庭关系,可能是父母离婚了,或关系本身就很淡漠,也有的人运气不好,甚至家庭里有暴力的情况。我其实非常能理解,经历过这些事情后,他们就不会对人产生信任,也不会伸出想了解他人的触角。
刘海龙:我在《逃走的人》的豆瓣评论里提到,李颖迪笔下的许多人像是"减配版"的数字游民。数字游民是个比较中产阶级的话题:他们逃离一个环境,前往山明水秀的地方,试图重建自己理想的生活体系。他们依然积极社交,试图建立新的秩序。
但我在读这本书时会感觉,很多人不是在逃离地方,而是在逃离关系,逃离人。我能感觉到采访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很多人不愿意跟你说话,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交往。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影响,鹤岗的寒冷决定了他们好像不是特别热情,也给了大家一个不用跟人打交道的理由。一些人可能是在过去的人际关系中受到一些伤害,便没办法期待去跟人建立关系。而那个地方经济又比较落后,冬天又特别漫长,就更不需要跟人交往了。
詹姆斯 · 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提到,历史上,国家要统治高地和高原地区的成本极高,即便征服了,也难以获得经济利益。久而久之,这些地方便成为"三不管"地带,因地理屏障而避开了统治。一些因战争、赋税等原因被压迫的人,就会逃往这些高地。
但今天,一些"被遗弃"的地方,因经济落后、发展"佛系"从而成了新的"高地"。与斯科特所说的不同,过去是因为交通和通讯的不便让这些地区成为避世之所,而如今,正是网络的便利,让人们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
当一个人来到这样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和所有人都没有了现实联系,反而只能依赖网络与社会建立联系,甚至解决吃饭、工作等基本需求。换句话说,网络反而创造了一种数字时代的高地。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分化。其中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游民,比如做二次元的、汉服的,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做得很好,只是选择了一个生活成本相对低的地方;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工作,也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这部分人就属于我说的"减配版"的数字游民,他们还得依赖现实。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在数字化时代被制造、被建构起来的高地。随着经济下行,这样的"高地"或许会越来越多,成为社会提供的隐居之所。

电影《再见瓦城》
逃离从来都在发生,只是主流叙事让它显得不正常
李乌鸦:刚开始我其实不太喜欢《逃走的人》这个书名,因为听起来有些太负面了,好像是因为我打不过,所以要逃跑。但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一种人生选择。
书里写到一个后来去鹤壁的男生,他原来在生产线上工作。我就想到我父母也是生产线上的工人,但他们当时不觉得人生有那么多的选择,也不觉得在生产线上的工作很痛苦。而我们现在有了选择,所以才有了痛苦。人离开原有的生活路径,去做一种新的尝试,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李颖迪:我是出了这本书后,才很意外地发现原来大家对"逃走"这个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个很中性的词,是一个动作,而非形容词,形容的是人的状态和行动。例如艾丽丝 · 门罗写的短篇《逃离》,你也并不会觉得逃离是个错事。
刘海龙:这也涉及到叙事的问题。我们会把生活划分为主流和边缘,主流叙事就像刚才乌鸦讲的,比如父母那代人会觉得这件事是理所当然,不这样又能怎样?对他们来讲,上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孩子,抚养孩子,这是一个套装,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好像进入这条路是别无选择的。如果你没有完成其中一环,就会有社会压力对你说你该怎样,这个叙事就被建构起来了。
还是说回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他说这些人也并不是逃走,只是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们的传统叙事是从国家层面出发,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而逃离则是偶然、反常的。但反过来想,国家的形成需要很多的条件,而离开反而是一种更自然的状态——一个地方待得不好,就换一个环境。因此,逃走从来都在发生,只是主流叙事让它显得不正常。
另一方面就是选择的问题。弗卢塞尔的一本书讲到一个观点,他说从存在主义的角度,什么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去选择的自由。比如你是一个画家,你的自由体现在哪儿?并不体现在你去做公司职员,或政府官员,或扫垃圾的人。一个画家的自由体现在你在画布上怎样能超越自我,怎样让你的内在爆发出来,让大家看到新的可能性。这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种认为我有选择,这就是自由的,比如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城市;还有一种自由是我要在这个范围内做得最好,努力突破这种局限。
我前段时间听到窦文涛的一个演讲,他说他的很多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之中做出的,当时也觉得走投无路,前面没有答案可以抄,这就逼着你去想办法,很多东西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然后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自由,就是把你逼到绝境上,你怎么找到一种解决的方式。
这涉及两种自由的对话。例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完全脱离体制,成为隐士;而"名教之中自有自由"则强调,即便遵守社会规则,依然可以在其中叛逆。比如一个写作者,白天上班,但在写作时完全自由,表达毫无束缚。许多逃离的人或许实现了前一种自由,但未必达到了后一种,因此即使到了世外桃源,仍然感到受限。
李乌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挣脱了一个枷锁,以为枷锁之外就有非常广阔的天地,但真正让你自由的东西,可能就在那张画布之上,在于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只有找到自己爱做的东西,才能享受到这种自由。
但我也想说,这太难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属于自己的那张画布在哪里,也没办法从绘画、阅读、创作中获得那个更广大的天地。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就像书里说的,可能无法选择我要什么,但可以先选择不要什么。
李颖迪:刘老师的话让我想到我很尊重的两位写作者,胡安焉和周慧。胡安焉曾经送过快递,周慧也在工厂里工作过,他们在这两年都出版了自己的书,写过去的经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当我看他们的书时,会觉得文学是他们很重要的精神支撑,让他们更自由、更强壮。但书里的这些人,当我们成为朋友,我和他们交流时,会觉得这样的条件似乎是很奢侈的。
比如书中做客服的常州女孩,她读的是中专,她所接受的教育里,没有人会和她说你应该去读书,也没有人告诉她你怎样做才能更开心,你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当她辞了职,到了鹤岗,有了时间之后,她首先去画画,也去养水母,因为她觉得这些东西是美的,她想要追求一种精神世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不提倡我们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刘海龙:我之前提到过写作和绘画,但其实这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找到自己的兴趣。前几天我看了电影《出走的决心》,主角就是喜欢开车到处走,在行走中找到自己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寻找。
以前讨论的三和大神,他们可能也处在一种过渡状态,你不可能永远过无意义的生活,每个人都要去寻找意义。三和大神更像我说的第二种状态,在一个体制内进行反抗,很像斯科特研究的那些人,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弱者的反抗,你让我去干这个事儿,我就不干,或用其他方法搪塞你,由此获得一种胜利。可能在主流看来是这一种阿 Q 式的胜利,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实现了自我,在对抗中不那么服从。
反而是书中这些出走的人,我觉得他们更决绝,甚至更勇敢。为什么说是勇敢?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可追求的东西,希望改变自己的状态,最重要的是,最后还是要获得人生的意义。当然,意义是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去写作、打游戏、画画、旅游,甚至可以做手工,但追求之路是共通的。越是这样逃离的人,他们对意义的向往可能越强烈。而三和大神反而已经看透了,觉得出逃也是无意义的,还不如过一种无意义的生活,这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但问题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外来者,突然没有根地进入那个地方,你会发现你很难建立一个人际连接,比如通过网络、微信群,书中还有很多人打游戏、直播、开网店。读完这本书给我一个感觉,就像证明了韩炳哲讲过的一段话,他有本书叫《叙事的危机》,大概意思是数字媒体或数字的表达,它是没有故事、没有叙事的,仅仅通过网上形成的连接是脆弱的,没办法真正获得情感上的支持,或生活的意义。
书中的一些人每天打游戏,直到服务器休息才停下来,但他们依然不满足,始终觉得缺少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意义的追寻",需要体现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书中的好几个案例往往由于原生家庭或生活环境造成的困扰,特别决绝地切断了和现实生活的一切关系,但他们在这个地方也没办法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就会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电影《大佛普拉斯》
现代人际的"拼凑"与孤独
李乌鸦:我好奇的是,两位怎么看待来鹤岗的这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人际关系是何种程度的需要?大家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会一起去朋友家吃饭,一起玩剧本杀,但这其乐融融的背后又有另外一面。
李颖迪:我觉得是一种有限的需要。鹤岗的微信群就像是你刚讲的那种聚落,每个群里都有几百人,会分享哪个装修队靠谱,哪个坑人,哪个中介收两千块,哪个收三千块,哪里停水了,这些生活中的信息。微信群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连接方式,大家也会在群里认识朋友。但最后关系能深入到什么地方,在我当时待的那个节点,会感觉大家的关系还是很松散的。
在鹤岗时,大家就很像是搭子关系,比如看电影搭子、去公园搭子、打牌搭子,都是这种临时拼凑起来,共度一段时间,并不深入,然后就分开的关系。
刘海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和媒体也有关系。当没有数字媒体,我们只能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的交流范围有限,就必须要维持这样的关系,因为你不维持,就没有关系了。但有了网络之后,就有了我们所说的"趣缘群体",大家只用交流喜欢的话题,不涉及其他,也对彼此不感兴趣。这是两种交流方式,现在第二种方式会越来越多。但大家从小生活在网络时代,会感觉好像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流。
人和人之间如果是现实的关系,当然会有一种亲密感,但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和付出更多。你受伤的时候是可以去倾诉的,但反过来人家有这样的需求,你也得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付出。但现在的一个大趋势就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拿来就用,是即插即拔的 U 盘式的关系,这可能和整个世界都在走向个体化有关,每个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考虑一切。
我觉得不仅是《逃走的人》里很多人是这种状态,整个社会都在走向这种状态。但对个体来说,也可能导致情感支持、社会支持越来越弱,当你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人来听你倾诉,也没有人帮你解决问题。
李乌鸦:我读这本书时,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书中的很多人都"不典型"。过去我们在纪实作品里,比如译文社关于日本"孤独死"的系列报道,会形成某种刻板印象,但这本书里的人并不符合这种印象。甚至,有些人相当乐观,会主动建议"多和人接触"。
在阅读过程中,我更倾向于把每个人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例,而不是某个群体的代表。当 Ta 做出看似悲哀的人生选择时,一定有 Ta 自己的理由。
包括颖迪在书中也引用了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里的话。这让我想到,那些令人遗憾的故事,往往源于某种未解开的"结"——而这些结,大多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正如刘老师提到的,只有在线下,我们才清楚关系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往往都伴随着某种付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 Youthology,作者:小纠,编辑:阳少